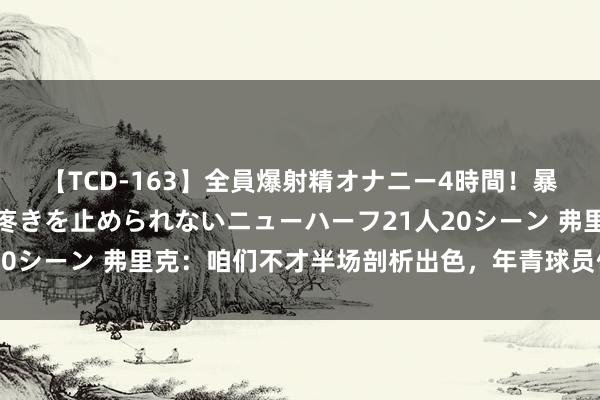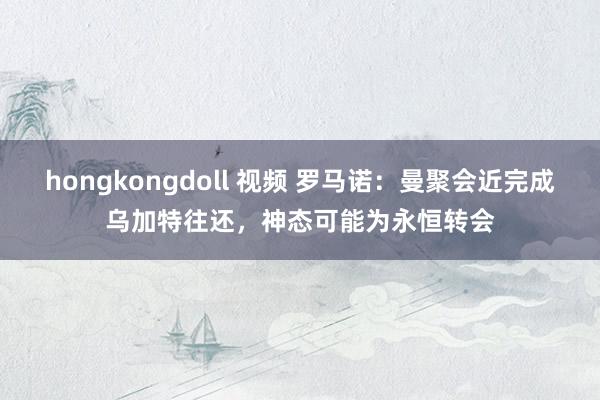![【TCD-190】黒ストッキングが似合う女子校生は美脚ニューハーフ コンプリートBOX 古风故事: 雁千里 [完]](/uploads/allimg/240806/060A94301041K.jpg)
我叫雁千里【TCD-190】黒ストッキングが似合う女子校生は美脚ニューハーフ コンプリートBOX,二十三岁,是启国天子最宠任的男宠,权倾朝野。
天启二十八年,贤良赵将军因对我不敬,被暗里攀附我的大臣坑害标谤下狱,朝堂东谈主心惶遽。
启王年逾六旬日益昏庸,已萧瑟朝政多时,整日流连后宫苟且享乐。
春宵帐暖,好意思东谈主在侧,他仍不得志地捧着我的脸含情笑。
我抚着古琴面带含笑,回看他的眼神书不宣意。

图源采集 侵权删除
1
一日又得启王传召,命我去八百姻娇的清养殿抚琴同乐。我应诏,抱着古琴慢步穿过宫廊。
这时一小宦官急匆促中跑来拦住我的去路,只听他诚心规劝谈:「雁千里大东谈主请止步,瑾王殿下现正等在前列。他与您素来顶牛,为注重引起不必要的突破,我们照旧绕谈走吧!」
瑾王裴昭,二十四岁,先帝的第九子,亦然目前圣上启王最小的弟弟。
「他如何总结了?」我皱了蹙眉。
「是啊,出征了两年,前些日子刚奏凯回朝,如今风头正盛。别传因为赵将军的事对您颇有不悦,我们这样顺利撞上去只怕会赔本。」小宦官解释谈。
「怕什么?光天化日、皇宫大内,他难谈还敢杀了我不成?」我柔声安抚谈,仍旧谈笑自如地往前走。
竟然没走多远就遇见了裴昭,他似是已在那儿等候多时,一碰头就拦住了我的去路。
「雁千里大东谈主请止步,本王已在此等候尊驾多时。」
见他心情不善,我把琴递给一旁小宦官,俯身参拜谈:「不敢当,微臣拜见谨王殿下!」
「你是什么身份,见了本王还不跪下!」他样子冷落,声息冰冷。
启王曾赐我免跪之权,一旁的小宦官想替我解释,我朝他摇了摇头,听令照作念。
他走向前来,抬手捏住我的下巴,冷笑谈:「雁千里,针对赵将军的标谤是你授意的吧?是你一直在背后邪言劝诱皇兄,屡进诽语摧毁贤良。」
我扬起始来盯着他的眼睛,缓缓谈:「微臣不敢!」
2
不得不说,目前这个男东谈主确乎担得起一句如圭如璋、威武超卓,如果他的瞳孔里莫得毁灭起那么重的杀意的话。
竟然,他冷笑一声谈:「不管你敢不敢,本日本王都要替皇兄除掉你这个阻挠朝堂的苦难。」
「请王爷谈判明晰,这里是皇宫!」我谈。
「那又怎么?」话音刚落,他抬起一脚猛地踹向我的心口。
这一脚力量刚猛,可我莫得侧目,在飞身撞上廊柱后又狠狠跌落在地上,嘴里呕出了大口鲜血。
周围的宦官们都被目前这情形惊呆了,发怵真出大事,东谈主员迅速分为两拨:一拨忙跑去找启王透风报信,另一拨则赶过来致力约束。
裴昭似乎也怔了旋即,缓过神后还欲向我围聚。
小宦官们迅速飞扑曩昔将他拦住,死死抱住他的大腿苦苦伏乞:
「还请谨王殿下三想,那雁千里大东谈主但是陛下的心头好。如果真打出个好赖,追随们的命倒不足惜,生怕伤了陛下和王爷的昆季情分。」
「闪开!」裴昭叱咤着试图挣脱,但宦官们铁了心拦着,抱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让他一时半会儿计上心头。
这时我坚决从地上爬起,擦干净了嘴角的鲜血,重新跪直了肉体。
我俩眼神死死地盯住对方,就在两边僵持之际,一个小宦官气喘如牛地跑来通报:「谨王殿下息怒,陛下有请!」
这里距离启王休息的清养殿不远,想必他那里如故得到了音书。
裴昭整理了一下衣衫甩袖而去,走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脸色复杂。我低下头去避让他的目力,样子莫得半分波澜。
这件事很快就被传了出去,闹得沸沸扬扬,标谤与力挺裴昭的折子均满天飞。
启王不胜其扰,临了以裴昭私闯宫闱无故行凶,是对陛下大不敬之罪罚俸半年禁足一个月,又为平息公愤无罪开释了赵将军。
3
七天后的夜晚,我一个东谈主站在寝殿的窗户旁静静地望着夜空。
在不雅察到商定的信号后,火速与负责策应的宫东谈主换好衣服溜出了皇宫。
我先被东谈主领去了一处僻静的宅院,再通过内部复杂的密谈来到一个房间,而裴昭早已在此等候我多时。
此刻他已卸下了冷峻坚韧的外壳,造成了牵记中平和善良的形貌。
一碰头他立即起身迎了上来,二话没说先小心性掀开我的衣服探查伤势,轻声问谈:「还疼吗?」
我摇了摇头。
「我其时明明给了你时代,为什么不躲?若不是我看你实在莫得躲开的兴味实时除去些力,成果不胜设计。」他谴责谈。
「无妨,我没那么容易死。况且只好伤得越真、伤得越重才越有劝服力,赵将军对殿下的感佩之情也才会越深。」我答。
那一脚在我的胸口上留住了一块纷乱的、类似于玄色的瘀青,裴昭看得皱紧了眉头:「不行,我得再给你上点药。」
「不必了,御医如故上过了。」
「这药不通常,是我外祖父当年军中秘方,对这类伤有奇效。」他十分宝石。
我不再约束,问起安稳事:「赵将军那边如何?」
「嗯,如故出来了。他这次算是透顶对皇兄寒了心,对我戴德涕泣,在我派东谈主试探下也颇披涌现接济之意。」他一边替我上药一边回答。
「那就好。」我笑了笑。
「屈身你了颜忱,让你这样为我笼络贤良。」他的话语里带着几分歉疚。
「殿下何出此言?帮殿下亦然在帮我我方。只盼殿下早日正中下怀,为我颜家翻案申雪。」
「你安心,一定!」他承诺得无比坚定。
4
是的,我根本不是什么启都琴师雁千里。我真名叫颜忱,是前兵部尚书颜回之子。
十年前父亲被奸贼污蔑参与镇南王谋反一案,我颜氏一族被判满门抄斩。
在砍头前一晚,幸得我父亲的相知——裴昭舅舅的坦护才留得一命。他冒险用一个和我仪容相似的死囚替换了我,保住了我们颜家惟一的血脉。
离开监狱前父亲拉着我的手千叮咛千叮万嘱,让我一定要找机会为颜家平反申雪,否则他无颜下去面见已故的列祖列宗。
因我擅长音律,被裴昭舅舅以琴师的身份养在汉典。他暗里对我尽心教悔,让我开通政史、鼓诗书。
裴昭那时常来舅舅家串门,我也因此与他结子。我俩脾气相似、歙漆阿胶,在日常的相处中成立了稀有的少年心情。
本以为能一直留在他们身边,可十七岁那年,我在汉典抚琴时被前来私访的启王看中,被强制纳入了宫中。
我虽千般不情愿,但想着大略能以此为机会替我颜家翻案,再大的辱没也咬牙忍了过来。
过后我曾无数次找机会向启王炫夸当年谋反案的疑窦,可他昏庸极度,莫得半点想要彻查的兴味。
我发现在他眼中那不外是戋戋几百条东谈主命良友,他根本不在乎!
我深感报怨,在与裴昭的书信中炫夸出了轻生之意。
5
裴昭将我从山地边上拉了总结,致力劝说我活下去,并第一次向我败露了我方的抱负。
他痛斥我方的皇兄昏庸窝囊、刚愎私用、亲庸东谈主远贤臣,落拓官员退让赈灾款,放任无辜匹夫成片饿死。
他说不肯看到先人基业毁在皇兄手上,他需要我的匡助,邀我共谋大计。
我答理了他。
从那以后我便初始搜肠刮肚、极尽攀附之能事取悦启王,在他的偏疼和落拓下渐渐执政中有了一隅之地。
目前朝中名义看来主要分为两党,差别以太子和我为中心。
而我只是看上去声量大,太子才是信得过掌捏实权地位褂讪之东谈主,在绝对实力上对我有着碾压之势。
我俩平时相成绩彰,只消我对他改日的皇位构不成威胁,他就对我的作念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外太子看似安枕而卧,实质已群狼虎视。
因为高深的第三股势力早就冬眠在了他的周围,那就是裴昭在这些年间黑暗发展的,由朝中看似中立的大员们构成的暗党,此时已颇澄净象。
裴昭目前作念的就是在我的掩护下削弱太子实力,同期壮大自身。
这次拉拢赵将军就是一个伏击节点,意味着收效的天平如故初始缓缓向我们歪斜。
6
替我耐烦擦完药,裴昭先用帕子擦干净手,后从怀中掏出一把纯金打造的龟龄锁递过来:「这个送你!」
我一愣,打趣着说谈:「刚被罚俸半年,劝殿下照旧省着点花,这种华而空虚的东西以后照旧别再送了。」
「无妨,家中莫得妻室,一东谈主吃饱全家不饿,不怕揭不开锅。」他也打趣着答。
我光显他的宅心,负责谈:「不外是算命先生的天方夜谭罢了,殿下何须贯注?」
这是在我小的时候,也曾被一街边算命之东谈主测出有夭折之兆。某次当成见笑讲给裴昭听,没意想这东谈主还真记在心上了,有事没事送我龟龄锁。
「拿着吧,不为别的,就当戴身上好玩。」他看着我,魄力极度坚决。
我圮毫不外,只好无奈收下。
我俩又照料了一会儿要紧事,看到天色不早,我起身告辞。
「且慢,」他蓦然约束谈,「还有一件要事。」
「伏击的事刚才不都谈完毕吗?」我有些疑忌地看向他。
「不是朝堂上的事,」他有些徘徊着谈,「不外想问问你……你吃晚饭了吗?」
我笑了笑:「来不足了,如果启王蓦然前往我殿中探望,那勤苦可就大了。」
「刚才探子来报,今晚皇兄歇在张贵妃宫里,如故睡下了,多迟误一会儿也无妨。」
我回忆了一下,我俩确乎如故很久没一齐吃过饭了。
「那好。」
7
筵席快速被摆上桌,简直都是我喜欢的菜色。其中不乏许多我少时喜欢但在宫中吃不到的特质小食。尝了几口,滋味十分正统。
我心中一暖,说谈:「这样多年曩昔了,没意想你还铭刻我的喜好。」
「其实直到上菜之前我都还有些狭隘,不外幸好,这些年你的喜好并未改变。」
「是啊,你说奇不奇怪?东谈主都变了,喜好竟然没变。」我谈。
「在我看来你东谈主也没变,至少我在你身上感受到的照旧和当年通常的纯良诚恳。」
「殿下谈笑了。」我谈。
「我是负责的,」他答,「那日见你受欺凌,宫里那么多东谈主自愿涌过来改造你,抱着我的腿死不撒手,情真意切,可见你平日里待他们不薄。」
「都是同情东谈主,互相庇佑依偎取暖罢了。」说罢我不停起笑意,专注地埋头吃饭。
「对了,」裴昭蓦然启齿谈,「我前段时代在外头新得了几匹好马,铭刻以前你喜欢与我一同出门策马,不知近来可有时代?」
「不了,如故许多年没碰过了。以前本领就不精,现在更是迥殊了,我看还能不可跑起来都是个问题。」我谈。
「不要紧,我教你。」
我忙摆了摆手阻隔:「再说吧。」
告别后我回到寝殿,把他送的龟龄锁顺遂往我的好意思妙小匣子里一扔。晃眼一看,这几年裴昭送的龟龄锁竟在雅雀无声间攒了满满一匣子。
各式大小各式式样都有,甚而连地域特质都不尽相通:有华夏的西域的南疆的北境的,每一把都独具特质雅致极度,想来打造它们应破耗了不少心想。
不外果真徒劳了他一番苦心,因为我根本不想龟龄百岁,甚而恨不得算命先生说的那天早点到来——我早就活腻了。
现在的我每天亲近佞臣摧毁贤良,委身于一个恶心的老翁子,作念着从前我方最贱视的事,活成了我方最痛恨的东谈主。
我早就脏透了,我活得真的好累。
8
日子看似水静无波,我和裴昭的议论也在暗里密锣紧鼓地激动着。
不知是否察觉到了什么,近日太子一方频频向我发难,针对性地打压了我几个伏击的喉舌。
怕他赖事,我也顾不了这样多了,强行着手干涉了他几次东谈主员调遣。
太子勃然震怒,梁子算是结下了。
为了注重太子暗里对我进行报复,裴昭不但搜肠刮肚在我身边安插东谈主手加强对我的保护,还亲身干与我逐日的布帛菽粟,好意思其名曰查找可能的蛛丝马迹。
终结太子的报复没等来,他倒先出于「好意」差点把我害死。
比如知谈我爱喝冷酒,他不知谈从那处弄来一个可以自行发烧的银杯送我,终结用过几次后银杯内的发烧石泄露,与酒斗殴后有微毒,害得我吐逆脱水了三天三夜;
又知谈我有失眠症入睡不毛,他送了我助眠的熏香,况且拍着胸脯保证我方试用过没问题。终结我对那香过敏,焚烧一根顺利昏睡了两天两夜;
又知谈我爱奇花「鲛东谈主帐」,他不知谈从那处弄到了一巨额移植到我方府中。不外这次受害的倒不是我,「鲛东谈主帐」极其眩惑蚊虫,通盘王府包括他我方全被叮得满头包;
……
我迅速叫停了他的「好意」,况且实在想欠亨一个平日里魂销目断、冷静自持的东谈主如何会犯这样稚子的失实?
看着他逐日故作拖沓地顶着满头包招摇过市,还果真让东谈主……哭笑不得。
9
时代一晃就来到了八月,启王照例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启都秋猎活动,乌衣子弟及伏击大臣完全要参与其中。
太子和裴昭自不必说,每年都是狩猎的竞争主力。我作为启王的宠臣不必参与狩猎,只是需要骑在有时由宫东谈主牵着作念作念方法散散心良友。
那天太子看我的眼神一直充满深意,直观让我感到不妙。直到开幕式的鼓声响起我才知谈这个危机源自那处——他在我的马匹上动了当作。
提神了这样久,原来竟是在这里等着我。
本来暖和的马儿听到鼓声蓦然失控【TCD-190】黒ストッキングが似合う女子校生は美脚ニューハーフ コンプリートBOX,强制挣脱了牵马的宫东谈主,发了疯似的往猎场外跑。
这匹马自己就是良驹,速率奇快。又是在发了疯的状态下,一般马匹根本追不上,很快它就把追来的世东谈主远远甩在了死后。
我隐匿在了所有东谈主的视线,莫得所在。
它驮着我莫得方针地飞奔在偏僻的森林,所行之路坑坑洼洼,路上断枝横行、险峻遍野。
很快我的一稔也被树枝险峻等划得褴褛不胜,肉体被大面积刺伤,全身像被刀割通常弄得鲜血淋漓。
可我顾不得那些,抱住马鞍紧紧贴在马背上,拼了命躲过那些横断在半空的粗壮的树干。可以说一朝撞上,九死无生。
可就这样任由它疯跑,我朝夕也会被颠下去,这个速率摔到地上也绝莫得生还的可能。
10
不知在报怨中行驶了多久,我听到死后有马蹄声传来,距离我越来越近。很快那东谈主就追上了我,驱策着马匹与我并行。
「颜忱听我的,双腿夹紧马腹,坐直肉体,后仰拉紧缰绳。」裴昭的声息里带着剧烈的喘气,看来为了追上我他亦然拼了命了。
「不行,我作念不到。」我现在死活存一火,璷黫一动都有可能跌下去。
「别发怵,我在你身边呢,我会保护你。」他对我高声说谈。
他声息里的冷静和坚定奇他乡抚平了我的惊慌,给我注入了勇气。我渐渐冷静下来,拼凑坐直起肉体拉紧了缰绳。
「对,这样很好,听我指点别往前看。」他链接说谈。
但是如故晚了,我的眼睛下贯通地往前一滑,立马吓得心情乌青脑袋一派空缺:前边是一处深不见底且无法逾越的绝壁。
他的马儿察觉到了危机,自觉减缓了速率,阻隔往绝壁上冲。可我的马还在疯跑,似乎临了的方针地恰是那片绝壁。
前路必死无疑,可裴昭还在努力拍马跟上。
此刻我也慌了,忙冲着他呐喊:「快停驻裴昭,不要陪我送命。一切都是命,我认!」
「勒紧缰绳,别说傻话!」他专注地驱策着马,并未罢休。
但我俩此时如故拉开了距离,他的马缓下了速率,听任他如何拍打也不肯往前冲。
我放下心来,扭过火去,在马匹的飞奔中紧紧地闭上了眼。
也好!
11
可很快他的声息又在耳旁响起:「来不足了,快把手给我!」
我一愣,睁眼一看,原来情急之下他竟脱下外套蒙住了马儿的眼睛。马儿看不见路,在他的鞭策下闷头疯跑,是以很快追了上来。
「你疯了?」
开心色播「没时代了,快点!」他冲我伸出了手。
看着他心焦的眼神,我下贯通地把手伸了曩昔。
下一秒,一股强劲的力量把我从马背上拽了出去。我像是被抛到空中,又被他伸手稳稳接住,接着我落到了他的有时,撞到了他的怀里。
「小心了,攥紧我!」
我听话地搂住了他的腰,接着他掀开了保密马眼的衣服,死死地勒住了缰绳。
马儿吃痛又受惊,抬起前腿仰颈嘶鸣。在这片刻的刹那,裴昭抱紧我趁势滚下了马背。
马背下是一段长长的长满青草的陡坡,裴昭抱着我一直往坡下翻腾,他把我紧紧地护在身前,独自承受了绝大多数的撞击。
就在我滚得昏头昏脑将近失去贯通的时候总算停了下来,我俩都因为眩晕外加惊吓过度瘫在那里无力革新。
我趴在他胸口上,他搂着我,我俩紧紧贴在一齐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刚才……真险啊!」他有些后怕地惊奇谈,半晌后又缓缓接了一句,「还好你没事。」
我对刚才的事也心多余悸,顺手拔了一些草扔到他脸上,谴责谈:「你不要命了?」
他把草从脸上拿下去扔到一边:「看到你有危机,我就想不了那么多了。」
我的眼睛蓦然就有些湿润,望着朦拢的太空喃喃自语:「殿下不必如斯,为我这样的东谈主不值得。」
他再次捏紧了我的手,声息不大但实足负责地说谈:「颜忱,为了你什么都值得。」
12
我的马摔下了绝壁,且归的路上我骑上了他的马,他拉着缰绳缓缓地走在前边。
我俩心照不宣地享受着这旋即的颓败,四周景色如画,空匮间以为世界间只剩下我俩二东谈主。
「还铭刻吗?你刚初始学骑马的时候我也像这样替你拉过缰绳。」他蓦然启齿谈。
「是啊,一晃好多年曩昔了,没意想我一连点前途都莫得。」我无奈地摇摇头。
「要不就趁现在我重新教你骑马吧?」他抬起始来望向我。
他的头发在刚才摔得有些凌乱,就这样抬起始望着我笑,眉眼间恍然多出了几分生动的少年气。让我不由获取忆起了与他片刻相伴过的,纯挚的少年时光。
「好啊!」
说干就干,可不知是刚才被吓傻了照旧怎么,我竟全然忘掉了基本功,一初始老是频频滚落马背。
裴昭也不活气,我一摔就跑过来接住我,我俩笑着在草地上滚作一团。
13
自后在他不厌其烦地尽心教悔下,我总算捡总结了一些基本学问手段,竟也有模有样地跑了几步。
自后他干脆也骑上马,带着我在郊外上驰骋,让我在拖沓的安全感中追赶到了风,体验到了久违的开脱。
「喜悦吗?」他问。
「喜悦。」
「你如果喜欢的话,等以后……」他对我说着什么,可风太大,我没听明晰后半句。
「你说什么?」我在风中高声喊谈。
他干脆从死后环住我,把嘴巴贴到我的耳边高声说谈:「以后我时常带你来策马!」
「好!」我大笑着回答。
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因为我婉曲看到了辽远找来的侍卫。
差别的时候到了,裴昭难割难分地把我抱下马。他负责地注目了我一会儿,然后笑着书不宣意地指了指我方的脖颈处。
「什么兴味?」我有些不明。
他莫得回答。
夜晚我躺在床上番来覆去睡不着,仔细揣摩他阿谁动作的含义。
临了灵光一闪,那家伙,这是想让我戴龟龄锁又不好兴味直说。我好气又可笑,忙从匣子里翻出一把来挂上。
14
太子对朝堂的机敏度比我们设想中的高,似乎如故婉曲觉察到朝堂多出了一只无形的手在威胁他的地位。
他变得极为警惕,时刻寄望着各方动向。裴昭这边就变得极为被迫,他不肯再隐忍,数次提倡想要顺利站出来戮力一搏。
五六分的胜算照旧太险,我劝他再忍忍,因为我已嗅到一个机会,没准可以暂时困住太子。
旬日后有异邦使节来贺,那日启王准备了广泛宽宥典礼,邀请满朝文武于圣德殿中行乐。
饮至半酣,启王按照预先安排给各位亲眷大臣赐酒。为表示对他们的喜欢,命他的爱卿——我亲手投递——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酒是早就备好的,我接机在给太子那壶中下了药。此药名为「快活仙」,并非毒药,对肉体无害,是将近失传的南疆男女房中秘药。
此药无色无味,在体内代谢极快,一炷香时代内便会让服食者产生踏进快活瑶池的幻觉。
且中招的外皮弘扬也只是是体温升高、精神亢奋,与醉酒弘扬一致,过后追查起来也根本无迹可寻。
15
赐酒初始,分酒是按照座席次第进行的,裴昭的位置刚好在太子边上,按照次第我先把酒递给了裴昭。
在我躬下身去的时候不小心涌现了挂在脖子上的龟龄锁,裴昭看到后眼里线路出了刹那间的惊喜。
借着饮酒时宽袖的讳饰,他样子愉悦地盯着我,那眼神像是在说:你终于肯戴了?
我的脸瞬息就有些发烫,快速地拢好衣襟把它遮好。
这时裴昭蓦然举起羽觞冲着斜对面,大笑着谈:「张大东谈主,今儿欢娱,本王敬你一杯!」
话虽如斯,但他的羽觞暗暗瞄准的明明是我。
那坐斜对面的张大东谈主是个小官,和裴昭素来忘我情。被蓦然点名敬酒弄得有些昆季无措,忙站起身来闻风丧胆地回话,惊慌间酒洒了一地,惹得四周官员捧腹大笑。
果真稚子极度,我在心里对着裴昭无奈地摇头。
分完他,下一个轮到的就是太子。
16
我把御酒递给太子时,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竟笑着对我说谈:「本殿下本日也欢娱,特赏雁千里大东谈主也喝一杯。」
说罢接过酒壶亲身给我倒了一杯。
我微愣一下,笑着回谈:「此乃陛下亲赐御酒,是天大的荣宠,微臣不敢僭越。」
「无妨,父皇一向对你喜欢有加。一杯酒良友,他是不会谴责的。」太子把杯子递了过来。
我莫得去接,侧头望向启王,只见他正专注于玩赏歌舞乐妓的饰演,并莫得刺目到这边。
「大东谈主不喝,难谈是这酒里有毒?」太子的脸色蓦然变得有些异样,口吻也变得夸张起来。
「如何会?太子殿下谈笑了。」
「那就喝一杯。」
正在徘徊间,一旁的裴昭见状笑谈:「一杯酒良友,侄儿身份珍视,何须与这不关要紧之东谈主僵持?要不让皇叔代饮,偶合替侄儿试试内部有莫得毒?」
说着就要伸手来接。
太子迅速伸手阻扰:「皇叔且慢,侄儿怎敢劳驾皇叔?照旧让雁千里大东谈主替我们一试吧!」
说罢看向我,「雁千里大东谈主请!」
我知谈再不喝不行了,否则裴昭一定会想方设法替我喝掉,于是心一横,端起羽觞一饮而尽。
我把杯子倒转过来展示了空杯底:「太子殿下这下安心了吧?」
太子笑了,说谈:「我当然知谈这酒无毒,刚才只是和雁千里大东谈主开个打趣,想必大东谈主不会多心吧?」
「当然不会。」我答。
17
搪塞完太子,我攥紧时代分完剩下的酒,回到启王身边时如故有了点发烧的苗头。
我借口想替世东谈主抚琴,启王当然欢然答允。
趁着准备的本事,借着帘子和琴台的掩护,我从袖中掏出一支细钗。深吸连气儿,闭上眼睛猛地将它扎进了我方后背脊骨处。
此药无解,但可通过剧烈的凄冷使我方的意志保持清亮,让我方不被药物影响。
在细钗刺入肉体的刹那间,我痛得全身盗汗直往外冒。痛得目前发黑耳朵嗡鸣,嘴唇褪去了血色,心情惨白如纸。
琴室的帘子有破绽,破绽处偶合对着裴昭。今晚他欺诈各式机会频频往我这边看,当然刺目到了我的极度。
他趁着世东谈主不刺主见时候抛来了好几次温雅的眼神,我冲着他挥了挥衣袖表示我方莫得大碍。
我简直用尽所有的力气才让我方保持拖沓,剧痛之下每动一下肉体,每拨弄一次琴弦都是一次剧烈的煎熬。
不外力气总算莫得白搭,一曲未完太子竟然失控。他在令人瞩目之下公然起身飞扑在场舞姬,甚而现场宽衣解带欲对其行不轨之事。
海外使节和朝中大臣纷繁惊得急不择言,启王震怒,当即命东谈主捉拿太子。
现场依附于我的言官无须授意,自觉站出来旁求博考,标谤太子德行有亏、目失仪法、有损我天朝好看……
裴昭的东谈主也当令出来助攻了一波,两方你一言我一语对太子的邪恶层层加码,处罚建议也越说越离谱,甚而连废太子都提倡来了。
启王当然不可能听他们扯谈,临了下令暂停太子手中一切职务,让其安心闭阁想过三个月,其间不得与任何东谈主斗殴。
太子被架走的时候,裴昭脸色复杂地看向我,应是光显了一切。
18
饮宴已毕,我抱着琴走出大殿的时候痛得几近虚脱。
走过偏殿时,一个身影以迅雷不足掩耳之势把我拉进一个空屋间。
他捂住我的嘴,在我耳边轻声谈:「是我。」
我听出了裴昭的声息,点点头。
他把住我的后背把我拢至胸前,压柔声息贴着我的耳朵凶狠貌谈: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瞒着我擅自行动。你想过莫得,事情要是败露我只可马上反了来救你?」
他的手刚好碰到了我后背的要紧处,我耐不住痛哼出了声。
他立即反馈过来,忙把我松开:「我早发现了,你刚才在帘子后对我方作念了什么,那处伤到了?」
我此时如故痛得有些站不稳,通盘东谈主顺利靠在了他的身上。他立即扶住我,小心性掀开我的一稔,在看到我的后背时倒吸了一口寒气。
「对我方下这样狠的手,你可果真……」
「否则如何办,你难谈想看我也失控吗?」我强打起精神打趣谈。
「还贫?」他简直有些无奈了,「你忍着点,我先帮你拔出来。」
我点点头,被他小心性挪到墙边,把双手撑在墙上贯串他。
他想了想,从后头把小臂环过来伸到我的嘴边,小声谈:「咬着点,一会儿会很疼。」
「不必,我忍得住。」我阻隔谈。
「听话,否则我忍不住。」
拔钗的历程是另一种煎熬,我咬住他的小臂,痛得几近昏迷。
在细钗拔出来的刹那间,他竟比我还平凡自如,抬手擦掉了额头的盗汗。
19
裴昭的胳背被我咬出了血迹子,不外他似乎胡为乱做,看也不看地用袖遮住,然后熟练地从怀里掏出药膏来替我抹上。
凉凉的药膏抹上去很快后背就变得麻麻的,痛感顿时隐匿了泰半。
抹药的时候他一直莫得谈话,想来还在活气。
我只得主动启齿谈:「抱歉,这次的确是我自作东张,不外好在终结还可以。太子被囚住了,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空闲大干一场。」
他抬眼瞥了我一下,依旧莫得回复。
我蓦然意想什么,问谈:「如果说我今晚真的失慎暴露了,你真的会立马反了来救我吗?」
「说不定。」
我扭过火去看着他:「别犯傻。」
他停驻了手里的动作,盯住我的眼睛负责谈:「要不你试试?」
我把头扭了且归,通盘肉体背对着他:「还请殿下以大局为重,否则这些年我所作念的一切所有没特兴味兴味。」
他千里默了一会儿,蓦然把我通盘东谈主掰了曩昔。他把双手按在我的肩上,微微俯下身来平视着我,谴责谈:
「如果你死了,那你认为我作念的这些就特兴味兴味了吗?」
我蓦然有些呆住,看着他的脸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时他放在我肩上的手蓦然松开,将双臂环到我背后,紧紧地抱住了我。
「你以前说过,要和我联袂走到临了。可我心里想的却不单是是议论的临了,我还想要更远。
「是以我不允许你夭折,不想看到你有任何无意,我想让你一直陪在我身边,直到……临了。你光显吗?」
我莫得作声。
他莫得比及回复,微微嗟叹了一声,退而求其次谈:「那以后一直戴着我送你的龟龄锁好吗?你戴上它,我就能陪着你。」
「好。」
房间外长廊上的灯笼蓦然我方灭火了,房子里瞬息堕入一派黯淡,我俩就在这样的阴黑暗紧紧相拥。
我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负责地感受着他的呼吸和心跳。
「颜忱?」
「嗯?」
「以后你就会光显,我对你的尽心从来都不单是说说良友。」
「嗯。」
20
差别以后,我独自走在宫廷孤苦的长廊上,怀里还残留着属于他的浅浅的余温。
凉风一吹,余温散去,我仿佛又坐窝清亮了过来。
他对我那点难以言喻的情怀我不是不知谈,甚而在幼年时就婉曲有感。
可我俩之间隔简直在太大的沟壑,大到我不敢去想,大到难以逾越。
且不说这些年作为娈宠的挫辱已让我身心俱疲,就算到了那一天,功成之后,我是恶名昭著的前朝奸佞,是东谈主东谈主得而诛之的不幸。
我如何有好看存留于这世上,满朝文武又如何能容得下我?
如果到时候他非要保住我,又该如何面对这世间的质疑和攻讦?那样太自利了,我不肯那样谢世。
是以我一直都光显,陪他走到议论收效的那一天已是我生命的极限,哪还有什么更远的以后?
21
太子被解任禁足后,他的仇敌坐窝遭到豪恣的会剿和计帐。
动静太大,暗党以及背后的裴昭终于隐秘不住浮出了水面。
但也无所谓了,只消过了这三个月,一切将会尘埃落定,我们将会以最小的代价正中下怀。
这段时代并不需要我挡在前边作念讳饰,是以我能作念的并未几,逐日只安心陪着启王肉山脯林。
那一天我如平常一般插足启王寝殿,只见太子如故阴恻恻地坐在那里等着我。
他手里拿着传位诏书,一旁躺着中毒猝死的启王。
也对,太子又那处会是那任东谈专揽割的羔羊?
不外他直到现在才觉悟反击,似乎有些太晚了。
「低估你了雁千里,和裴昭这一手言行一致玩得妙啊,把我和我父皇所有蒙在了鼓里。」
我看清景色回身就逃,殿外裴昭给我安排的死士察觉不合坐窝杀进来掩护我。
我光显我方如故不容乐观,叛逃并非想要奔命,而是想办法见知裴昭太子异动,议论提前。
太子方东谈主数繁密,死士抵触不了多久。好在他收拢我的前一刻,我如约将信号发了出去。
铁心一搏吧裴昭,只需记取你答理过我的,替颜家翻案。至于其他的,功成不必有我。
「你可以杀我了!」任务完成,我平凡自如地迎向太子,准备安心性接管我方的运谈。
太子朝我冷笑一声,然后我就被打晕了曩昔。
22
我从剧痛中醒来,发现我方被吊在了一个地下暗牢里。
我不知谈这是那处,只知谈刚才我方被东谈主生生撅断了手腕。
一个凶神恶煞的狱卒告诉我:「关于你这样的苦难,太子打发不可让你死得太舒坦!
「你安心,这个地方绝对荫藏,听任别东谈主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是以不要抱着任何的荣幸。」
我遭到了严酷的折磨,胳背和双腿也均被撅断。那样的凄冷无法言语,历程中我几次昏死了曩昔。
后头的折磨我似乎没什么嗅觉,只知谈全身被戳了许多谈口子,皮肉外翻、鲜血淋漓,施刀极为有手段。
「拖沓受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说完那东谈主竟关上了牢门走了出去。
在他走后,暗牢的顶上蓦然开启了一个闸门,从闸门中不停有水往下泄。
我终于光显他为什么给我划那么多流血但不致命的口子了,因为在水里伤口不会凝固,血会跟着水流一直往外淌,直到流尽为止。
我别传过这种严刑,它对囚犯的肉体和心灵进行双重折磨。
跟着水位的上涨,即便不会流尽血而死也会被淹死。在这之前,还可能因为对示寂的忌惮活活把我方吓死。
竟然够狠!
也好,我这些年违心作念了许多的赖事,本来就不该得到善终。
23
牢里连一点后光都莫得,睁眼闭眼没什么区别。我干脆闭上眼睛默数着越来越轻细的心跳,少许少许地恭候着示寂的莅临。
静下来似乎能听到辽远杀声震天,这里应是皇宫近邻。不知过了多久,夷戮之声渐渐平息下来,我朦拢听到了「瑾王殿下万岁!」这样激动又整都地呼喊。
看来是赢了,我的心蓦然就完全减轻了下来。
此时水已膨胀到了腰部,按照这个速率不到半个时辰便会将我完全团结。
淹至胸口时我简直如故感受不到我方的呼吸,就在跌入不朽漆黑的前一秒,我听到了牢门翻开的声息。
然后耳边响起了裴昭练习的声息:「颜忱,再宝石一下,我来了!」
……
我一个东谈主在阴黑暗行走了很久,在几次差点坠入山地之前都被一个声息拽了总结:
「颜忱,快总结,裴昭需要你!
「颜忱,你要宝石住,我在等你!
「颜忱,你答理过我要陪我走到临了,你不可口血未干!」
……
睁开眼睛,发现我方躺在练习的床上,一大堆御医正围着我忙前忙后,裴昭则正趴在我床边酣睡。
24
我的苏醒引起了房内世东谈主的一派惊呼。
「终于醒了……」
「太阻扰易了,再熬下去老汉就得先走了。」
「我们陛下亲身守了他整整两个月啊,老天开眼。」
……
这样的动静当然也惊醒了裴昭,他似乎还未在睡意蒙眬中完全醒过神来,但眼里已先行流下泪来。
「醒了?」他的声息里带着些困顿的抽抽泣噎。
内宦当令地挥退了御医,我方也缄默地退到了一旁。
「你瘦了!」我艰苦地对他说出了醒来后的第一句话。他现在通盘东谈主不但瘦了一圈,还胡子拉碴的,看上去像是老了好几岁,显得无比报怨。
「不伏击,你醒来就好。你知不知谈有好几次气象都不吉无比,我差点以为就要失去你了。」他用手胡乱地抹去眼泪。
「你是如何找到我的?」我问出了我方昏迷之前最想知谈的问题。
太子的性格我明晰,即便裴昭赢了,即便对他如何威胁拷打,他宁死也绝对不会吐露关系我脚迹的半个字。
「他的确把你藏得很荫藏,可幸好你戴了这个。」他翻出了挂在我脖子上的龟龄锁。
「送你的每一把龟龄锁都是我命东谈主亲手打造的,中枢处都锻入了一种特殊的磁石,可以用特殊的磁盘感应。只消你戴上它,不管你在海角海角我都能找到你。」
「每一把都有?」我有些诧异。
「是的,每一把都有。还铭刻我说过的话吗?只消你戴上它,我就能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艰苦地笑了,然后也流下泪来。
25
可即便救回了我,我们面对的问题依然莫得处治。
以后我是遮掩耳目去一个莫得东谈主贯通我的地方?照旧他打算把我关在某个密室里再也不要出头?
「御医说你这样万古期醒不来是因为你自己的求贸易志不彊。我知谈你在费神什么,坚信我,一切不毛都可以处治!」
「是吗?」我凄切地笑了笑。
「现在大家都知谈雁千里如故死了,他在令人瞩目之底下目一新地死在了地牢里,你很快就可以堂堂正正地作念回颜忱了。」
「陛下当真以为这样可行吗?朝堂上所有东谈主都见过我的方法。强行识龟成鳖,他们不是笨蛋。」我不禁感叹裴昭的灵活。
「听我说颜忱,事实上我早在几年前就如故为这天作念好了准备。从你进宫的那一年起我就安排了东谈主手扮作你的方法,假名『永生』去了一个偏远的小镇生存。
「镇子上的每一个东谈主都认得你,都能为你这几年在那里的生存作念出佐证。
「到时候只需要『永生』拿出左证阐扬我方就是前兵部尚书之子颜忱就行,你本来就是真的,当然能提供充分的左证。
「那时候那些东谈主能质疑你的点就只剩长相了,可这世上长相相似的东谈主何其多?我早就找到了至少三位与某朝中大员长相极其相似之东谈主,到时候偶合可以用来挑剔他们。
「总之铁案如山,你的身份经得起任何探访。你阿谁如故故去的雁千里莫得任何关系,你就是可信无疑的颜忱,他们想不承认都不行。」
26
我被他这番精细的议论惊呆了,愣在那里很万古期说不出话。
「你是什么时候初始议论的?」我问。
「我若说在你入宫的第一天,你信吗?」
我的脑子蓦然就很乱,通盘东谈主也像醉酒一般晕晕乎乎的。
「我从未想过要将你藏起来,以前没告诉你是发怵吓到你。我说过我想和你走到临了,当然也会意想并处治这一齐上可能会碰到的报复。」
「真的会那么到手吗?」我照旧嗅觉有些作念梦般的不真实感。
「不知谈,不外遇到任何问题我都可以和你一齐面对,我是负责的,除了你的老套我什么都不怕。给我一个陪你走下去的机会,可以吗?」他轻轻捏住了我缠满绷带的手。
我莫得谈话,固然另一只手上还绑着夹板不便捷,但我依然艰苦地限定着它,把它搭在了裴昭的手上。
他如故为我作念了这样多,那我不管如何也不可在这个时候老套。
27
登基后不久,裴昭火速下令彻查当年镇南王谋反一案。还了以我们颜家为首的无辜被污蔑的官员们的结义。
一年后,朝廷根据痕迹在一个偏远小镇找到了颜家幸存的惟一血脉——假名永生的颜忱。
我的出现引起了朝堂的一派哗然,可正如裴昭所料想的那样,铁案如山,即便有东谈主质疑也拿不出左证反驳。
令所有东谈主诧异的是,我阻隔了朝廷给我抵偿的官职,自愿沦为一介布衣。
归正我所有的心愿都已达成——为眷属平反,甚而还堂堂正正作念回了颜忱。
至于其他的,功名富贵对我而言都是浮云。
裴昭虽有不明,但依然尊重了我的决定。
我住在他宫外那所有密谈的宅子里,他偶尔会溜出来陪我吃饭,而我也时常暗暗进宫与他畅聊一夜。
他实践了我方的承诺,有空就带我去猎场策马,在他的尽心教悔下,我的马术突飞大进,甚而婉曲有了与他并肩驰骋的实力。
在一个酒至微醺、愤慨息争的夜晚,我俩的关系终于又久了了一步。我第一次在那件事情上体会到除了辱没和污辱外千里溺又彭湃的欢乐,他调养了我。
他依然会时时常送我龟龄锁,而我欢然接管况且每天换吐项目地指导。
龟龄于我而言终于不再是吊唁【TCD-190】黒ストッキングが似合う女子校生は美脚ニューハーフ コンプリートBOX。